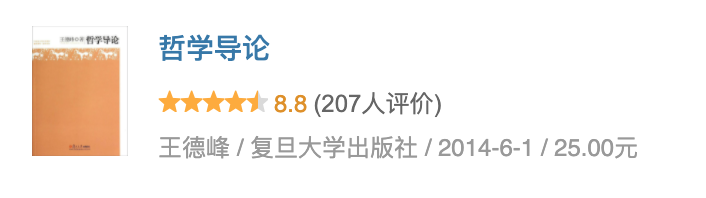灵感启发
相反相成返本开新要有他山之石。没有比较、对话,所谓深入的理解,只是空话。
体用逻辑太阳是因,阳光是果。但这种因果关系比较特殊。第一,它不在时间中。不是太阳作为原因之事先存在,而后有阳光作为结果跟随其后。第二,太阳本身不是可以直接被感知的东西,可直接被感知的,是阳光。
自因逻辑从世界本原学说到本体论的过渡,即是从对感性的第一因的探求到对费感性的自因的探求。
工具观念锤子对于人,作为一种实现敲打作用的中介物,是一种观念的存在,所以当某一种特定的锤子在人的视野中消失时,任何一样可用以敲打的东西都是锤子。
实体感念有确定性的东西,就是是在的东西,实在的东西就是一种实体。
存在问题
- 所谓追问存在问题,即是要追问那有待解释的世界之「何以可能」。
- 西方的本体论,其根本旨趣不是要探究出一个「本体」来,而是要说明存在者的基本规定。
- 始基就是万变之中不变的本原,是整个自然界变化过程的基础。这基础乃是一种单一的物质的东西。必有一种单一的宇宙物质,万物产生于它又复归于它,这可以说是被伊奥尼亚学派视为自明的假定。
- 存在者,即是被思维者。思维的对象,表面看起来是感性事物,其实却是客观思维。感性事物之所以能够被思,是因为它被客观思维所规定,即它成了能存在者。
- 感性实在之为感性的,必定是杂多而具体的,故必须是杂多而具体的,故必须抽象掉一切感性的具体性和杂多性,然后把被抽象了的“感性实在”本身立为绝对者,才能有「物质」范畴,否则,就又会退回到拿某一种特定的感性事物当做“本原”的“前本体论”中去了。但经过对一切感性具体性的抽象,这个作为绝对者的「感性实在」,其实就不再是感性的了。可以,物质之为物质,归根到底还是思维规定。
- 这个我,作为纯粹思维之我,使意欲、感觉、想象、走路成为我的。我是在这些内容中的思维。这些内容是具体的我,我是具体的我中的纯粹意识。不能说,我走路所以我存在,而应该说,我存在,所以这走路的是我。
道器问题
- 与思想本身异质的东西,通常只是显示器,而不是澄明者。澄明是思想自身的努力。澄明必须从显示器入手,但要避免听任思想迷失于显示器中。
- 直接的文化创造及其产物以实际功能构成人的现实生活。这些创造物(从日用器物直到社会典章制度),人们创造出他们,而后受用他们,同时也受制于他们。
人的矛盾
- 最根本的生存的两歧有三种:一,生与死的矛盾;二,人的长远想象与人的短暂生命的矛盾;三,根本上孤单的个人与他必须与他人交往的矛盾。
- 存在性忧虑:一是对死亡和命运的忧虑,一是对空虚和无意义的忧虑,一是对内疚和罪责的忧虑。
- 生存的两歧也好,存在性额忧虑也好,说明的只是一个基本实情,即,理性在虚无面前暴露了自己的根本有限性。
人的文化属性
- 欲有所明,终有所蔽,不应畏惧。
- 文明是人的生存方式。人的生存方式不是自在的自然自身的一种形式。文明意味着超出自在的自然,包含着自在的自然不可能有的新的东西。
- 人只作为生物存在的自然起源,不可直接说明人之作为有文明创造力的存在物的起源。
- 文明作为人以改变生活类型的方式来适应外部条件的创造性活动,是在本能贫乏这种生存之否定性的基础上,达到生产性的自我决定的自由。因此人就必须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由他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世界中。
- 动物在自然界中的存活方式与人在自然界中的存活方式的区别就是本能活动与劳动的区别。
- 意识惟有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存在才有可能达到自我认识,意识只有达到自我认识,它才同自然意识本质地区别开来而成为精神,而这一点正是也只能是通过劳动才达到的。
- 对象一旦被劳动着的意识所规定,并且通过陶冶的中介过程完成此规定,它对于意识就不再是绝对的他物,而是意识的“为我之物”。精神正由此诞生。精神之本性也由此揭明:所谓精神,就是在异己的东西认识自己本身,在异己的东西里感到是在自己的家里。
- 作为人的人,是有文化创造力的人;有文化创造力,就是有文化生命;有文化生命,意味着有理想,有关于人的理想。
- 若一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失去了人生理想,或只以动物式的欲望满足为“理想”,那么他们就丧失了真正的人生奋斗,即丧失了把自己提升到人的高度和尊严的奋斗,这个民族的文化生命就处于衰竭之中。
工具:人心中关于物与人之关系的观念存在
- 类人猿的工具活动在主观方面也同人的工具活动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包含判断、推理、预见和回顾。但是,这种高级的智力活动,在类人猿的意识中只是一个片段的、非连续性的心理过程,只是对于偶然的、一次性的“工具情景”的应对。“工具情境”是有限的感觉知觉范围,在此范围内,类人猿能够去估量形势,形成计划,付诸行动,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后,事情也就随之结束。所以类人猿对于工具的需要属于一次性的情境性需要,工具对于它的存在也仅限于这种外部感性显现的范围。在类人猿的心理生活中尽管已有某些预见和记忆的萌芽,但在根本上无法摆脱out of sight, out of mind的基本状况。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 在人那里,工具也必须是可感的外部物体,必须具有感觉形象,但是,工具不限于这种感性的存在,它更是人的心智中的观念。这“观念”并不是指工具的感性外观在人的记忆中的心理表象,而是指人的活动与自然物的“关系”在人的心智中的存在。为人的心智所把握的这种“关系”构成人的观念。
- 每一种特定的感性的工具都不是工具本身,而是其特定的感性显现。所以人们必定要不断地去改变工具的感性特征,使之尽可能地接近于工具的观念原型。这就表现为工具的一个进步过程。
- 所谓工具只观念的原型,不可误解为这种原型是在人心中的工具表象,表象还是感性的东西,只不过是在记忆和想象中的感性。观念之为观念,不是指这种东西,而是指对一种特定的“关系”之在意识中的把握。工具的进步,其实是力图让物体的感性特征更接近于实现对这种“关系”之在意识中的把握。
- 文明不是建立在人对外部世界的感觉知觉上,而是建立在关于自身活动与外部自然的“关系”的自为意识上,这种自为意识就是观念。
- 观念之为观念,即在于它不是在时间过程中被感知的外部自然之物,它是超越感性的、非时间的因而是不朽的东西。
- 工具在感性外观上的变化、消失、不会使工具在人的心智中消失。作为观念存在的工具是不朽的。
经验并非天然而来
- 大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之打交道的事物,都是实际的事物,对实际的事物形成经验,就是“识知”。识知总是对于外部事物的经验的判断,例如,判断“这是方的”。这一判断要能形成,自然先要有感觉材料,要有外物在人的心灵中留下感性印象。但这一堆感觉材料本身是杂乱无章的,这外物究竟为何物,是无法仅凭这些感觉材料来判断的。感觉本身并不做判断,它只是形成对于外物的印象。说出“这是方的”,必包含非得自感觉的理解,即把这一组感觉材料同“方”的观念联系起来,然后才把杂乱的感觉构成一个别的此物,并将他判断为“方的事物”。
判断的来源
- 评价即包含尺度。尺度来自何处?来自对真迹的了解。如果我们老是被困在实际中,又如何可能去了解真迹呢?不了解真迹,又如何能发生对实际事物的评价,并提出进一步努力的理想目标呢?
古希腊哲学思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 思想的本性就是超越感性去把握唯一的真实体。
-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西方人心目中的「知识」的本来意义。思维的本性,在于它是对实在之真相的把握。这真相不在感性中,而是在为思维所把握的事物之本质中。人的思维之能力,即是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