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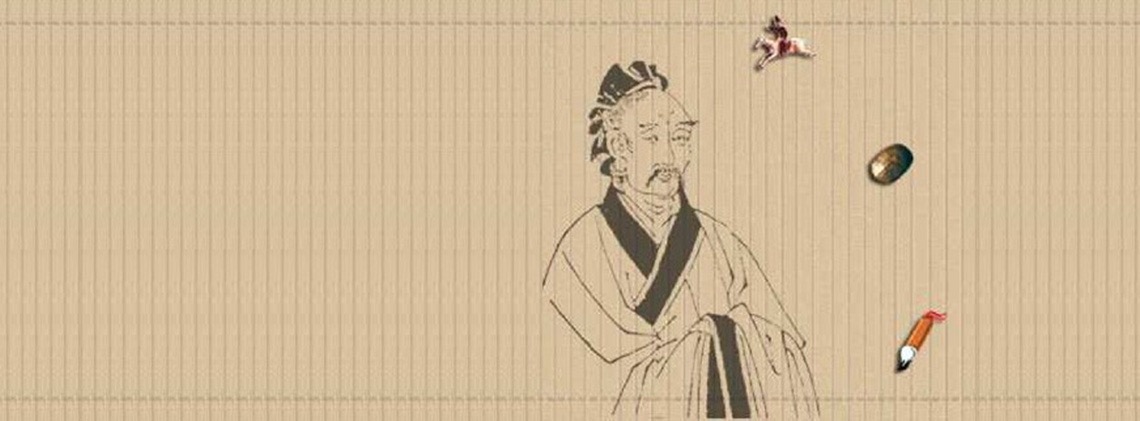
这个世上最精明的人往往不是满脑子塞满了莫名其妙的思想的哲学家,也不是精通炼金术的老学究,也不是智商卓越的天才,而是深入学习过历史的人。经验主义哲学家和孟子的论点都相似:人类生来就是一张白纸,生活的经验为其添上色彩,有些人拿起画笔,在纸上胡乱作画;有的人在提笔之前,先参考别人的画(如何画线条,如何着色,如何润色)。后者画出美丽的图画,前者只是一堆胡乱的红和绿。记录前人的生活给了当下人的生活最好的指导,这就和作画是一样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情,只要人性没有变化,人做的事情就会再次发生,只是换了个形式呈现而已。懂这些的人都知道历史会重演,他们要做的只是在此之前做好准备。
按道理,司马迁这个年轻时就游历四方并且饱读过春秋的人应该知道,在该管住自己的嘴的时候,不应该凭着激情与冲动表达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在面对一位性格乖张,脾气乖戾的年老皇帝的时候。然而在李陵这件事情上,他倒是失去了历史学家的冷静,为自己招致了灾祸。既然要死,仕人大夫也追求个痛快,然而他司马迁接受了奇耻大辱。后来他在书信中回忆起自己下这个决定的勇气:“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螘何以异”,并且苟且偷生下来。是的,人死了就是死了,跟蚂蚁没区别。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司马迁背负着重负,不愿意死得轻飘飘的。
从牢房出来的那个夜晚,我们并不能确切知道老实人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身体的痛苦可能使他难以思考,也许床头才写好一半的书简使他难以入睡。“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是否应默默的忍受坎坷命运之无情打击,还是应与深如大海之无涯苦难奋然为敌,并将其克服。此二抉择,究竟是哪个较崇高”,莎士比亚的名言在这时与他最为贴切,人类的群星闪耀就在此时。
痛苦消散之后,他肯定会记得他将要写或者已近写过那些人物和故事。这些故事他在青年的时候早就耳熟能详了,他们活跃在他的竹简之上,像是是一条干净的河流里面闪着光辉的石子,这些光亮映射到了后来人的眼睛,并且用他们对照自己的人生。卧薪尝胆的勾践,圯上纳履的张良,或者一夜悲白头的伍子胥,帝王们,将军们,复仇者们,如今安安静静地躺在他们的墓冢里,用自己的一生教会了司马迁和绝望中的人一件事:人活一世间“忍”字为先。所以当任安——他的朋友——向他求助时,他变得“聪明了”,他回绝为他的朋友求情的请求,倾诉了自己的苦衷,还附带了讲述了自己遭受的痛苦。可怜的人,痛苦的人,不完整的人,遭受了命运打击的人——他充满着悲愤地提到那些遭受了苦难又成就了伟大的事业的先辈,仿佛这些苦难就是为了伟大的作品得以诞生一样降临到人的身上。他还提到了自己为了完成使命而做的决定:“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他说:文王啦,孔子啦,屈原啦,这些人都是因为遭受了苦难,才成就的作品。它以这些人的事迹鼓励自己,因为此时他活下去并不是为了偷生,而是为了要完成他的父亲和自己的夙愿:写出一本上至轩辕皇帝,下至汉武年间,跨域三千年的中国历史。
我们的历史老师以前带我们读什么《公羊传》啦,《母羊传》的时候,就只想睡觉。这些枯燥的历史书籍就像是一个小学生写的日记,读起来如同嚼蜡。但每次我们读司马迁的史记,就不会觉得因为大部头而无聊,反而会觉得这些历史人物非常有意思,他们有血有人,嬉笑怒骂,成王败寇跃然于纸上。这些人物的传记,远比那些只有只言片语的,记录流水账式的《春秋》有意思得多。《史记》的另外一个我们喜欢的特点就是他不会以成功和失败去衡量一个历史人物。也许是因为自己的遭遇,悲剧性的英雄总是引起他的共鸣。例如把他把失败者项羽写成气拔山兮力的盖世英雄,并且将其安排在《世家》里面;又把汉高祖这位历史的胜利者的流氓本色揭露无疑;它即对儒家描绘的三皇五帝粉饰太平,也为豫让,要离等一些悲剧性的小人物立传记。在《货殖列传》中他写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俨然是一位古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真谛的洞察家。《刺客列传》里面又讲述了他写荆轲时收集到的史料为自己的故事佐证,俨然一位科学主义的考古学家。
人们能从史书里面对照现实吗?也许不能,中国的朝代历史仿佛是一条追逐自己尾巴的狗一样;欧洲也一样,在杀掉自己的国王的时候,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都干得干净,漂亮,出奇的相似。历史仿佛陷入了一个大循环中,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似乎就是:永远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况且在历史里面的又有多少真东西呢?
谁人知道姬昌是不是因为被囚禁才写的《易经》,又有谁知道躺在秦庭大哭的申包胥是不是真实的呢?张良有没有在桥遇到黄石公?上古时代的帝王是不是真的贤良如此呢?我的历史老师在评价这些古人写文章时总说他们是形式大于内容,为了文章好看而夸大历史。《史记》中充满了大量的人物对话,这在如今的历史学家中眼中会觉得不够严谨,毕竟人们都知道这些话很可能是作者自己添加上去的。我读书的时候也常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司马迁写历史不够严谨,甚至不如比他早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
但是后面越是读他的书,越是觉得这就是一本历史,甚至比真实的历史还要真实。它包含了人物的悲欢离合,就好像我们在和这些人有了情感一样,既有农民的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也有包含智者深情的劝慰:“人生一世间,白驹过隙,何必自苦如此”。它描写历史人物的言行,近而让我们看到人性在这三千多年中的,是如何不变的,就更太阳东升西落一样,亘古久远,历久弥新。另外,在实时收集上我们也见到了其方法,在荆轲传记里面他写到因为他从自己的祖父的朋友那里获得的关于刺杀请始皇第的事情,所以他将其与史料相结合写入历史。年轻时的游历以及对古籍的阅览,又增加了他的见识。在古代,一个世纪的变化往往如今这么大。树木,房子,山川河流,不会因为推土机或者城市建设而遭到破坏,所以,在真实性上我还是愿意相信这位究其一生都在追寻历史真相的专业学者。
有两种人最伟大,一种是生为既得利益者,却为了劳苦大众背叛自己的阶级,投身革命。另一种是抱着坚定的信念而忍辱偷生,用自己的余光照亮后人的道路;前者有孟德斯鸠,切格瓦拉之类,后者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司马迁以及其他的历史学家。他们都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在人类的历史上总是用来作为评判正义与邪恶的标准:增进绝大多数人类的幸福。

